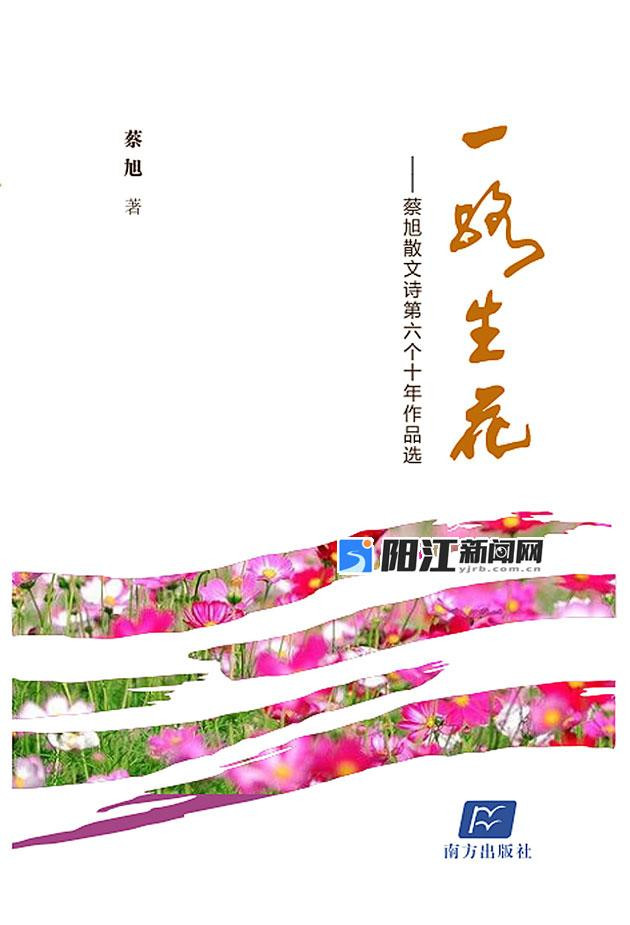
□ 胡红拴
在当代散文诗日渐陷入精致而空洞的修辞竞赛之时,蔡旭先生的《一路生花》以其散文诗创作第六个十年的实绩,提供了一种近乎异质的写作范式。这部作品选不是词语的炫技,而是生命的沉积;不是情感的即时宣泄,而是时间的缓慢结晶。蔡旭将散文诗这一轻逸的文体,锻造成承载历史重量的容器,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叙事中,完成了一场关于记忆、存在与文明的诗学辩证。
蔡旭的散文诗具有独特的“琥珀美学”。琥珀的价值不在于树脂本身,而在于它封存了远古的生命痕迹与时空密码。在《菠萝蜜的旅途》中,20世纪60年代的一列慢车,一件用旧报纸包裹的故乡果实,一次偶然的车厢分享,被诗人用文字凝固成永恒的瞬间。菠萝蜜的香气在湘赣线上飘散,金黄的果肉在陌生旅人手中传递,这不仅是物质的馈赠,更是文化的微缩迁徙。蔡旭的高明之处在于,他让一个热带水果的旅途,承载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——那种匮乏中的丰盈,封闭中的开放,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神奇转化。五十年后诗人的“津津乐道”,已不是简单的怀旧,而是对文明传播路径的诗意考证,一个微观的文化地理学样本。
这种“琥珀美学”在历史题材中更显其深邃。《听树皮屋讲往事》里,桂东北深山中那些用树皮筑就的房屋,既是矿工肉身的庇护所,更是国家记忆的档案馆。蔡旭不作宏大的历史评述,而是让树皮屋自身言说:“树皮屋给我们,讲住在这里那些挖宝人的故事。”诗人以物的持久性对抗人的易逝性,让建筑成为历史的活化石。当树皮屋从矿工居所转变为学校,功能的变化揭示了时代的变迁,但其中蕴含的开拓精神却如琥珀中的昆虫,形态鲜活如初。蔡旭的历史观不是线性进步论的,而是层积式的——不同时代的精神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的共振回响。
蔡旭的散文诗建立了一种“微物之神”的叙事伦理学。他笔下的事物往往具有超越其物理存在的象征维度,但这种象征不是强行赋予的隐喻,而是从物性本身自然生长出来的精神性。《炒米饼》中,一块普通的家乡糕点,因与冼夫人军队的传说相连,成为穿越千年的文化符号。同样,《珠海鱼摊》中杀鱼的过程被提升为一种民间技艺的审美仪式,摊主娴熟的动作如同“非遗”表演,日常劳动因此获得了近乎神圣的仪式感。
在人物书写上,蔡旭避免英雄史诗式的宏大叙事,而是从生命的细微处捕捉精神的闪光。《推轮椅走路的人》中,那个每天推着空轮椅锻炼的老头,他的坚持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尊严与爱的寓言。诗人不渲染悲情,不升华主题,只是平静地记录:“轮子动了,脚步才能跟上。”这种克制的观察,反而比任何激昂的颂歌都更能触动人心。对于历史人物,蔡旭也采取类似的“微观历史”视角,《三亚这座城市》不写风景的旖旎,而写黄道婆与袁隆平——一位解决穿衣,一位解决吃饭,诗人的城市叙事因此锚定在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上,获得了坚实的伦理基础。
蔡旭的散文诗语言具有罕见的“及物性”。他的词语不飘浮在现象之上,而是紧贴事物的肌理,在命名中让存在自身显现。《与白海豚共舞》中,对白海豚的描写精确而传神:“一米多长、百斤多重的大型哺乳动物,跃出海面是那么矫健挺拔,钻入水中是那么体态轻盈。”没有滥情的抒情,只有对生命形态的忠实记录。这种及物性在《桃花心木》中达到极致,诗人通过对木材纹路的细致描写,自然引申出“心里美”的生命哲学,物的特性与人的品质在语言的精准中达成和谐。
值得注意的是蔡旭散文诗中独特的时空结构。他善于在有限的物理空间中打开无限的历史维度,《外婆村》从一条普通村落写到番薯引入中国的宏大历史,空间因时间的注入而获得深度。同时,他又能在绵延的时间之流中捕捉空间的定格,《北极熊爬雪山》中熊孩子无数次跌倒又爬起的瞬间,被放大为关于绝境与希望的永恒寓言。这种时空的交织处理,使蔡旭的散文诗既具历史的厚重,又不失诗的灵动。
《一路生花》这个书名本身就是一个诗学宣言。花的香不是强烈的气味,而是需要时间酝酿的微妙存在,是物质与精神在时间中发酵的产物。蔡旭的散文诗正是这样一种“香”的制造过程——他将个人记忆、地方知识、历史碎片放入语言的容器,经过数十年的沉淀,最终结晶为这些充满智慧与温情的篇章。在这些文字中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诗人第六个十年的创作总结,更是一种生命态度与艺术信念的完美融合:真正的诗意不在远方,而在我们与世界的每一次细微接触中;历史的真相不在宏大的叙事中,而在日常生活的肌理深处。
当文学创作日益被即时性、消费性所支配时,蔡旭用散文诗的形式提醒我们:艺术的价值在于它对时间的抵抗与转化。正如琥珀将易逝的瞬间转化为永恒的物质,诗人用文字将流动的生命经验固化为可流传的精神形式。因此,《一路生花》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,更是一部关于如何生活的哲学手册——它教会我们如何在浮躁的时代保持凝视的耐心,如何在碎片化的存在中寻找连续性的意义,如何将个人的微小经历炼成普遍的人类智慧。这或许就是蔡旭散文诗留给这个时代最珍贵的馈赠。
展开阅读全文

网友评论
更多>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