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藤 子
《素食杂谈》,乍看封面,很是迎合当今潮流,“素食既有悠久的历史,又是一种有益健康的时尚”;细看书页,满是与某蔬某菜有关的历史典故。原为素食而来,一不小心“吃”下了一肚子的故事。
《素食杂谈》开篇作《谈“荤”论“素”》让我对“荤素”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,尤其是“荤”。“荤,臭菜也。从艸,军声”,作者引用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里对荤字的解说,是想说明最初的荤菜,不是今人所常吃的动物类食品,而是有强烈气味的可食植物,如葱蒜韭椿等。为何有强烈气味的菜被古人归属为荤菜之列,这又有许多典故可数,留待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书中与作者对谈。
素食,当它被后人窄化为蔬食,再被现代人尤其是盲目追求骨感美的女性尊为减肥圣品的时候,已变得寡淡失味了。那个能把菜根嚼出《菜根谭》之味的时代,离我们远去了,但那个明末隐士——洪应明,却在“去留无意”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他说“美女不尚铅华,似疏梅之映淡月;禅师不落空寂,若碧沼之吐青莲”,“为善不见其益,如草里冬瓜,自能暗长;为恶不见其损,如庭前春雪,势必潜消”,“藜口苋肠者,多冰清玉洁;衮衣玉食者,甘婢膝奴颜。盖志以淡泊明,而节从肥甘丧矣”,而最为我们熟知的大概是这句“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”了。
另一草字头的古代著作——《本草纲目》,其著作者李时珍更为后人所熟悉,此熟知大多是熟知其人名和书名。若不是看《素食杂谈》,我对李时珍的认知也只停留在小学课文《李时珍》里,知道他是古代名医,并牢牢记住了《本草纲目》这本书的名字,仅此而已。《素》书里,作者讲到的每种植物几乎都引用了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里的记录作为旁证,正如作者所说“李时珍不仅是伟大的医学家、药物学家,更是伟大的植物学家”。李时珍,湖北蕲州(今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蕲州镇)人,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(1518),《本草纲目》在他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漫长且艰苦的探寻与学究中,历时二十七年最终于万历戊寅年(1578年)完成全书的编写工作。1593年初秋,这位76岁高龄的老人告别人世时,《本草纲目》还在南京由书商胡承龙等人主持刻版,直到3年后才印出书籍。李时珍不仅是医者,更是学者、文人。曾经,我浸泡在离这位古代名医不远的黄州市里,却没去“拜会”过他。2008年的春天,去蕲春探望大学时的下铺“大哥”,又与当地人说的“李时珍陵园”擦肩而过。
回到我们的小城——阳江,这片被当地百姓常言“贵地总无忧”的土地,古今也出过不少文化名人,亦有外地文人名人在此客居过。《素食杂谈》里写豆芽菜提到徐渭(字文长)曾为他的一位靠卖豆芽为生的朋友写过一副奇特的对联:长长长长长长长,长长长长长长长。上联念:“zhang
chang zhang chang zhang zhang chang”,下联念:“chang zhang chang zhang chang chang
zhang”。写山药又引用了徐渭的《薯蓣》诗。这位明代著名的诗人、书法家、画家,曾在阳江官舍里(现江城一小)客居过三年(1540-1542年)。“记得阳江官舍里,熏风已过荔枝红”,这是徐文长在阳江时写下的诗句。“疯狂巨匠”“狂狷才子”徐文长,其名声在文人墨客圈子里几乎无人不知晓,且备受推崇。清朝放荡不羁、目中无人的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郑板桥,刻印章“青藤门下走狗”一枚致敬“偶像”徐文长(徐渭幼时在其父亲的书屋天池旁边栽下一株青藤,日后他写诗作画常以“青藤”“青藤道士”“青藤道人”等为别号);当代著名国画家齐白石说起徐文长也表示“……余心极服之,恨不生三百年前,为之磨墨理纸。如不纳,余于门外饿而不去,亦快事也!”
另一在《素》书里被提到的现代著名作家许地山,也曾在阳江客居过三年(1904-1906年),其当时住址大概在今天的南恩路。“原来我们离文人这么近。怎么老师教书时,没讲过”,一位陌生的阳江朋友早年在我的博客里写下留言。初中,老师在讲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时为“落花生”这一名称再三详说,她也不知道许先生曾在江城停留过,曾在青云路基督教开办的“证光小学”读过三年书,不然她一定会“再四详说”给我们讲述作家客居江城时的童年往事。自学《落花生》一文后,偶尔想起还是会对“落花生”感到疑惑,尽管可以凭原文中“花生可以榨油”来断定它就是我们日常所吃的花生,但为什么不直接用“花生”呢?《素食杂谈》里给了我倒序的答案:“我们常吃的‘花生’是豆科植物,开黄色小花,旋花下落钻到泥土下结成带壳的‘长果’,也叫‘落花生’,后又省作‘花生’”。《素》书里说到的马铃薯也曾被古人叫做“落花生”,典故自是有的,不在此赘述。
又《素食杂谈——烫手山芋》一文里,不仅讲到山芋,还讲到木薯,番薯。如果用“番薯”形容一个人,多少带点贬义。但是,有一位在阳江客居过的戎马作家——吴有恒,却甘愿当“番薯司令”。1949年10月,吴有恒同志率部队进入解放前夕的江城(阳江的正式解放在1949年10月24日傍晚),其时驻扎在今江城一小的一间教室内。吴司令秉承军人“军令如山”的作风
,发出的号令若属下执行不到位,必会受到他的一顿痛骂。后来,战友批评他,并劝其改正“不近人情”的作风。吴有恒是一位既持刀枪也舞笔墨的将军,刚硬中不乏文人气质,这样的作家型将军改起硬脾气来也是雷厉风行的,说改就改。有点将军脾气却无将军架子的吴司令,与群众关系融洽。招呼他吃饭无须大鱼大肉,有时一顿番薯就够了。吴司令可以吃番薯作餐。有时饿了,生番薯也照样吃饱肚子。他还风趣地说,生番薯其实并不比水果差,可以当水果吃,又解渴又饱肚。这种感情,和当时阳江的穷苦人民是很融合,因此,当地人都亲切地称吴有恒为“番薯司令”。
《素食杂谈》如一锅大杂烩,如其封底所言“读者诸君自可各取所需,喜做美食的,喜长见识的,喜听故事的,或许都可得到满足”。我是喜欢听故事的人,虽记性不甚好,也算在阅读的过程中长了不少见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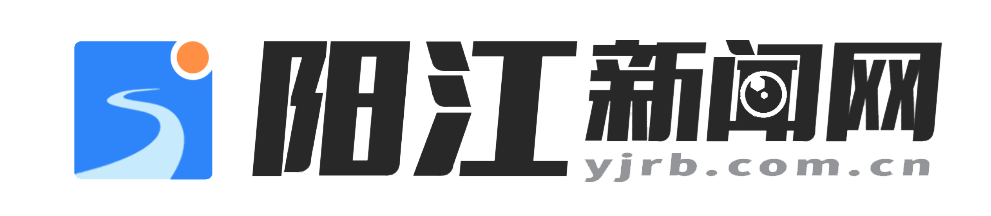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网友评论
更多>>